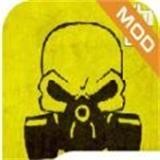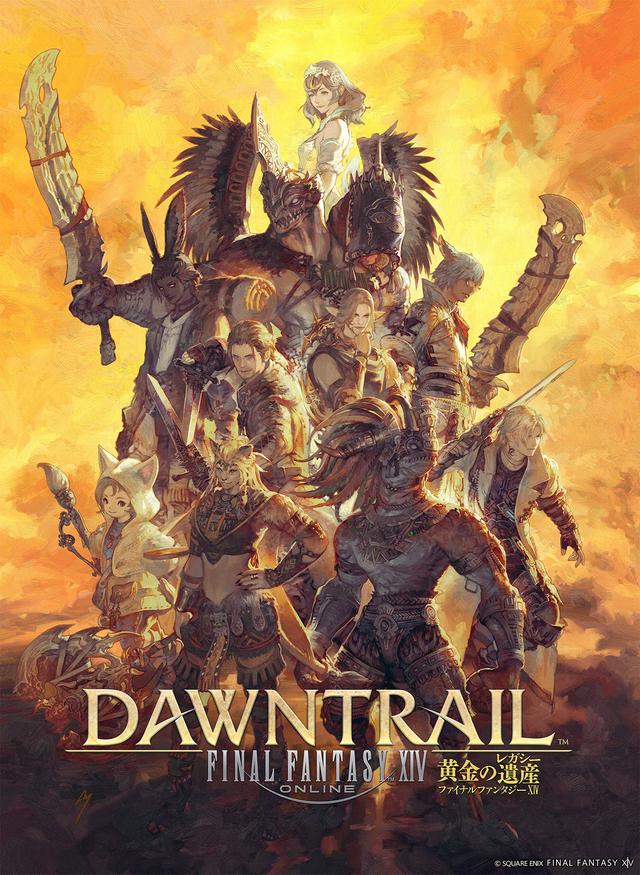第一军情特别推荐:
随着人民军队第89个生日的到来,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多年——这意味着,新中国诞生前那些“闹过革命”“上过战场”的老军人们,渐渐被岁月吞没或者正在做着人生最后的斗争。
有句著名的军谣唱道:“老兵永不死去,他只是渐渐凋零。”
的确,他们没有死,也没有凋零,他们只是退居在了他们自己的世界罢了。
第一军情作者郭继卫,就出生于那一代打过仗的军人家庭。在这个建军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与郭继卫一道,向他的父亲,向那一代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军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第一军情作者:郭继卫
一、怀旧隧道
我父亲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一个老兵,他今年90岁了。
家在一个熟悉的院子,这里有一个标配的名字——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入驻者是凭战功、至少是凭作战资历,赢得安享晚年的入场券的。
在小院中的咳嗽声都是有年份的,漂浮着某场战役的味道——远比制式的回忆录更动情地占有战事的真实。
它像一条怀旧隧道,在另一头贮藏着中国革命史当中最残酷、最壮烈,也最为匪夷所思的战争气。

父母住在一个空军干休所,父亲在他的老式军帽上,别了一枚过去的空军领徽。
若身在其中,可叹的还包括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变得衰老甚至狰狞,老“休干”本人、他的老伴、他的续弦、他的子女、他的保姆……甚至,包括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年轻护士变成了广场舞领舞,食堂小王变成了厨师老王……
一旦连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在这个院子里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的时候,说明老人们“带孙子”的最后一项社会功能也失去了。
父亲这几年“忽地”老了,在老式的宽大的沙发前,他显得愈加短小,想向前走两步,都是一步一蹭的。
他的记性已大不如从前,这是最让我惊悸且痛楚的。有些问题,诸如问我“你现在在干什么?”他会问好几遍。原以为他会对特别喜欢的孙女更“上心”一些——只不过,孙女现在在哪儿也是要问许多遍的项目。
很显然,爸爸的记忆力出了毛病。
组建了60多年的这个革命家庭,风雨飘遥。
以前那革命的冲劲儿、悍劲儿,在他们的屈从中碎了一地。

母亲(图右)1950年入伍加入公安部队,照这张相时16岁。
二、砸碎旧世界
我是家里的“老幺”,所以“错过”了这个家庭初创时期的许多记忆。而一旦要动笔触及过去时,才发现对“家史”有许多的盲区和忽略。
老妈1935年出生。1950年,妈妈从县城里教会办的“富育女中”报名投身抗美援朝,入伍后被留在了当时称河北省公安总队的公安部队,从那时起走上了革命道路。18岁时,与父亲相识、结婚。
那时,父亲是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的最早一批军官,从华北军区而来。他出生在华北大平原的深泽县。在当年,那个地方为“日伪”与“八路”拉锯争夺的区域,不当“八路”就当汉奸,几乎难有第三种选择。
父亲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在当时更加危险也更加艰苦的“县大队”抗日队伍,多少次与鬼子伪军短兵相接、死里逃生。最后,这些队伍战胜了小鬼子,守卫过西柏坡,打下了北平城。

父亲1950年从华北军区调入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这是授衔那年照的。
父母他们当然是这个新中国当中最年轻最优秀的一群。
我想象得出,刚刚诞生的国家,百废待兴的社会,二十出头的青春,蒸蒸日上的事业,他们曾是多么兴奋和激越。
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启始的时刻,军队被叫停了“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脚步。除了那一时代的伟人,许多军人和军属都没意识到:通过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四两拨千斤”,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悄然莅临了。
很快地,他们“战斗”的机会没有了。就如同从镇国的“专政机器”上拆卸的旧零件,给分解下来,然后将他们很负责任地收藏到了一个叫干休所的“仓库”当中——否则,遇到今年夏季的这些情况,他会吵着闹着,恨不得带人开着战机直接冲向南海。

父亲在南苑机场。
三、勇敢地“作废”
离退休以后的家庭生活,反而成了隔三岔五拌嘴的辩论赛了。我很难评价他们到底相爱不相爱、幸福不幸福。说他们相敬如宾是不可能的,和每个父母眼中都有一个乖孩子叫“邻居家的孩子”一样,我眼中也有模范的家长叫作“同学的父母”。
当然,他们也不是组织包办的那种“二八七团”(即所谓“28岁、7年党龄、团级干部”的结婚条件),他们风雨同舟一个甲子过去,特别是经受政治运动中彼此坚信的考验,甚至在“上级”动员他们“划清界线”“揭发批判”的时刻——那时他们有信仰支撑着,似乎是最“团结”的时候。
这也许可以视为,他们只是在革命挑战的超常态下,才充分显现出相爱与幸福的属性。他们不说 “我爱你”,他们说“我相信他听毛主席的”。这也勾勒清楚了怎样才是“正宗”的革命夫妻。

父亲在天安门广场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留影。
干休所的许多老头儿们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热衷于“谁是哪支部队的”,喜欢比“谁的军龄党龄长”“谁的孩子干什么工作”“谁的老婆有没有文化”等等。还有他们想当(娶)、或者传闻中他将要当(娶),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当(娶)的更高职务(更年轻媳妇),这一啪啦大小闲事,和他们的现状有个毛的关系啊?可他们就要为此喋喋不休,耿耿于怀。
甚至,当他们有什么事不爽了,就把专门伺候他们的干休所领导叫来骂一顿。干休所领导涵养超好,一口一个“老首长”哄着他们。曾有位干休所领导说过一句貌似颇为深刻的话:这几十上百万老家伙们都打过仗、带过兵,留在部队“添乱”,流入社会“危险”,撮到一堆成山,就只能放在一个个小院子里“关着”,平平稳稳、好吃好喝地变老。
在一二十年的“军旅后”更年期之后,这些曾经保养得不错的空军军官们也不可抗拒地开始面对每年逐渐减员的“干休所魔咒”了。这下子,他们才蓦然懂得,应当要比的是“谁活的时间更长”“谁的生活质量更高”,和“谁能领到新一轮上涨的离休金”。
仿佛,对比他们年轻时的得意,才凸显出他们暮年的呆笨和荒凉。

1952年,正在谈恋爱的父亲、母亲在北海公园。
四、被“献身”铸型
不会有人怀疑他们是共和国最初一代也是最忠诚一代人。革命、激进、笃信、自律、盲从……塑造了他们。他们是经过炮火的筛选、淘洗的淬炼,为了国家初创需要的奠基、铺路、粉碎、深埋所“订制铸型”的。
他们内心简单而炽热,无论是去赴汤蹈火,还是抛开自己的安乐窝,只需一个号召!
除了在性格上的“革命性”之外,他们的习惯也被凝固在了那个时代的的“艰苦奋斗”——和这个时代的“扣扣索索”上。他们的“节俭”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花椒在炒完菜还要捞出来用下一次;在洗手池下永远有一组水桶,每天用的水,全接到一个个桶里,佝偻着背的他们每天一桶一桶地提去冲厕所。这次回家带了盒海参回去,我们不怎么会做,烧出来偏硬,结果第二天海参被从菜里挑出来,剁成小颗粒出现在新蒸的包子馅里。

父亲在北京东交民巷老空军司令部办公楼前。
一切凑合不是目的。他们的离退休金在定期上涨,只不过,克俭自己是他们还能够做到的维系过去的唯一的快乐——那是他们漫长而有趣的节约战役。
改革开放,经济与文化突飞猛进。遗憾的是,既然没有物化的载体,光靠一两张报纸,是无法进入这个小屋了。
老了不可怕,旧的不可怕,被时代甩在老地方,那才可怕。
也许更可怕的,是他们故意要停留在过去。他们把玩、享受着某种被新型社会的抛弃感。这让他们更温暖、更从容地浸泡在从前的理想主义的春风得意当中。他们参加革命、从事工作,也许真的没有想到过荣华富贵、没有想到过光宗耀祖、没有想到过让自己舒服。
他们真纯粹。
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可悲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了。

父母在这个干休所已经度过了30个新春佳节了,其中绝大部分我都没在他们身边。
五、战备式生存
我想回家了、思念书信的那一头;
回家真幸福,在火车上站十几个小时算什么;
回家真温暖,好吃的菜、熟悉的床、恒定的摆设;
早早起床,不让出去玩,不能随便看电视,没有网络;
总是“说说话”“聊聊天”,又没什么新鲜话题、共同语言,闷死了;
东西太旧、太破,卫生习惯也不同了,他们真是out了;
这也说教、那也管着,想逃离;
告别了,总算松了口气……
然后,很快又重复到开始,周而复始。
这也许是很多军人家庭中很小年纪就出去闯荡的子女们的共同感受。
家,在我们眼里是个爱而不至于久留、怨而不能忘怀的矛盾之乡。和家的距离,是一种相吸相斥间纠结的停顿。

父母在60周年“钻石婚”结婚纪念之时,找出了当年空军为他们颁发的结婚证,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方形印章。
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是父母的什么意识把家塑造成这个样子?
他们建立这个家时,大国新定,不仅百废待兴,更是险象丛生。这造就了他们自认为 “时刻准备打仗”——其实那早已越来越是幻象。
在我们家,每个人都当过兵。他们给我制订的高考志愿基本都是军工类大学或军校,录取分竟然是先低后高的——其顺序是在他们的眼里看来的军事重要性——他们对教育和未来太陌生了。
从结局倒推可以证明,我们家庭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个孩子养成的能力和习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最适应、最显效的,那就是战争岁月!
我们都受到过部队训练,都懂得军事生活,都至少有一门军事技能,性情上还都不为婆婆妈妈的家庭儿女情长所羁绊。
他们没留神自己只是某一个阶段、某一种状态中的能手。当没什么需要他们捍卫的时候,最后必须捍卫的,就只剩下自己的态度了。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无奈与苍凉,胜过有条件、有能力为年迈的父母做些什么,而他们不屑接受、或反感接受的呢?
峥嵘往昔渐渐与老父亲无关,他正在把他最自豪的戎马旧事从近到远一堆一堆地丢散。我也曾试图让他多一些“时尚”与“休闲”的眼光,但无数的努力换来的是他不高兴、被冒犯。
一个时代需要一拨人。而这之后,他们仿佛就该让让路,一边歇着去了——这很正常。
然而,既然国家在走,众人在走,咱无论快慢都要跟着、都要携着、都要念着罢。
新时代,巨变快。炮火硝烟远去了、殊死搏斗远去了、狼犺老兵远去了。我们优哉游哉般生活在远远避开战争的岁月。
他们在艰难地完成耄耋老兵苍老内心的末段成长。当然,社会也需要去帮他们完成这一代英雄群体那最后的成长。
而我们怎样从老兵那里继承一种血性,去迎接下一仗?
至少,我们应当在建军节到来之际,给他们一个虔诚的军礼。
写给我的父亲,也写给他那一代老兵。